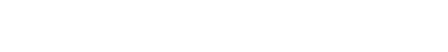唯邻史卜|明德识堂之中国书院变迁略述
时间:2021-05-26 来源: 浏览量:
2020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正式创建。书院联系四个人文学科院系,实施人文学科大类培养和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古文字方向)、历史学、哲学三个方向的培养。明德识堂将从多重视角逐一展现书院学生的思考、发现和实践。
中国书院变迁略述
明德识堂·唯邻史卜
写在前面:
学术界对书院起源问题的探讨
明德识堂·唯邻史卜
关于书院的起源问题,由于对于书院的界定不一等诸多原因,学术界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
1、唐代说:代表人物有邓洪波、陈元晖、罗晋辉、张劲松等,其中不同学者对于同时代书院的具体起源时间的界定也有差别。比如,陈元晖认为最早的书院是建于贞观九年的张九宗书院(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邓洪波以唐苏师道《司空山记》中的记载,断定“光石山书院是早于丽正、集贤的民间书院”,并提出“从现在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攸县光石山书院和蓝田的瀛洲书院、临朐的李公书院、满城张说书院一起,要算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了”(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罗晋辉则认为中国最早开展教学活动的书院是桂岩书院(罗晋辉《书院若干问题辨析》,载于《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
2、五代说:支持者认为以南唐升元年间建立的白鹿洞书院标志着书院的开始。周予同先生指出,“南唐升元中,因庐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亩,以集诸生,推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于是含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才开始出现”(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上海书店,1991年版)。包括章柳泉(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在内的一批学者也发表过相关的论述。
3、北宋说: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到:“(宋真宗)咸平四年,诏赐《九经》于聚徒讲习之所,与州县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王夫之有此观点,主要是因为他将书院归入了聚徒讲习的私学范畴。此外,徐晓望则主张“若儒家学者自办学府,并向广大民众开放,这类学府就可称为书院”;“就可靠的史料而言,目前只能说作为学府的民办书院起源于宋初”(徐晓望《唐五代书院考略》,载于《教育评论》,2007年第3期)。
4、其他:除上述三种较为主流的观点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认识。比如高慧提出:“就书院讲论学问、展开教学、传播文化、流通典籍等要素及其基本规制而言,诸端在魏晋南北朝私学中实已趋于完备。可以认为,后世书院无非是魏晋南北朝私学的继续发展(高慧《魏晋南北朝私学与书院起源的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只要是具有教学性质的机构和场所便可算为书院。由于影响力不大,仅加以列出,不多赘述。
唐以前:沉淀与酝酿
明德识堂·唯邻史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的国家。以教立国的思想为历代人物所重视。
《说文解字》:“庠,礼官养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孟子·滕文公上》:“殷曰序,周曰庠。”尽管两者记载有相冲突之处,但中国教育机构至少在三代就已经存在,这是基本无疑的。
春秋战国时代,民间私学的兴起推动了整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大转型。先秦诸子百家之所以形成,战国时代之所以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繁荣,与私学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主张“有教无类”的原则,以“六艺”授徒,弟子三千,可谓春秋战国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私学。这一时期私学的教学模式多样,包括讲授和游学等。孔子门生多继承其事业,讲学授徒。战国时期的孟子同样游学各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其他如荀子、墨子等都以所长立学设教,百家争鸣。
秦朝“焚书坑儒”,严厉的文化教育政策使得私学大幅衰减;秦灭汉兴,私学再度繁荣起来。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负责儿童启蒙教育的书馆、书舍;针对成人研修经学的精舍;大儒收徒、四处讲学……这些机构的兴办和大儒的贡献使得两汉私学得到极大发展。《三国志集解》(陈寿撰,裴松之注,卢弼等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卷六记载:“(刘备)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嘉靖淄川县志》(王琮纂修《嘉靖淄川县志》,嘉靖25年刻本)记载:“(郑玄)后游学淄川,居黉山,授生徒五百人,四方文学之士多宗焉”。另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之后又有鸿都门学等出现。两汉经学的发展与繁荣既与私学密不可分,也离不开太学这样的官方教育组织、学术组织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政权更迭频繁,官学“时兴时废”,门阀势力坐大,官学生对于门阀极为看重,而学生的出仕对于其成绩等不甚看重,学术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学。陈寅恪先生认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上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即公立学校之沦丧,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家学者是也”(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加之官府支持、通经致用的需求和佛道两家的逐渐兴起等多种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已经初步具有讲论学问、展开教学、传播文化和流通典籍等唐宋书院所具有的要素。
上千年的发展、沉淀与酝酿之后,书院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唐与五代:书院之始
明德识堂·唯邻史卜
关于“书院”之名最早出现的年代,论者多引袁枚《随园随笔》中“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一段文字。但邓洪波根据地方志记载,认为“攸县光石山书院和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张说书院”四所唐初的民间书院是中国最早的书院。
书院原本只是士大夫的私人读书之所,但渐渐向社会开放,接纳好友、学者、僧侣等一同聚会、品诗、研讨,书院逐渐成为公众文化活动的场所。
到唐玄宗时代,书院组织逐渐为政府所关注。长期以来,政府对于图书典籍都极为重视,汉代有兰台、东观之设,并且有校书郎等官职专门负责校勘等任务。到了唐代,中国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官府加大了对图书收藏、整理、校刊等工作的投入。官府也依沿汉魏以来的故事,在中书省推出了丽正、集贤书院这一全新的官府的学术文化机构。书院得到官府承认,逐渐为更多的士人所接受,遂使这一机构开始大量出现于民间。从开元六年到二十八年间(718-740),东西二都先后建有五处集贤书院,展开了盛极一时的文化学术工作,而且后此百余年,集贤书院仍在开展活动。作为官府的书院已然化入大唐的政体之中。
五代十国时期,离乱中的士人并没有就此心灰意冷,他们或深居山中传授知识,或出仕官府以传承礼仪风;而诞生于唐代的书院备受关注。此时的书院,继承唐制,大多数政权依然立有集贤(书)院,设有学士诸职,掌管刊印古今经籍。不过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恐怕难以展开实际工作。
两宋:书院的黄金年代
明德识堂·唯邻史卜
一、北宋
宋初,久乱初平,但宋朝并未完成真正的统一——北域辽国压境,西北疆西夏崛起。而连年征战又使得国库空虚,因此,宋初80余年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面对这种政府无力发展文化的状况,士人沿袭前代的做法,聚书山林,建院讲学。
于民间兴学的同时,北宋政府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一方面大力发展科举,增加取士名额;另一方面大力支持书院的发展。此时有“书院之称闻于天下”之说。新生于唐代的书院,以声名显赫之势,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同。
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北宋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再次呈现出繁荣局面。而北宋政府已经具备了恢复和发展官学的实力。更直接原因是“不务耕而求获”的科举制度。宋初无力兴学而大倡科举,但士人中也出现了贪图名利,不务实学的弊病,使科举走向了反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遂堕素业,颓弛苟简,浸以成风。”)。因此从庆历四年开始到北宋灭亡,开展了三次兴办官学(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的运动。
三兴官学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和发展完整的官学体系,并明确其权威性,进而以升舍之法取代科举考试,集养士取士于官学教育之一途。官学的普遍建立及其权威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书院不再替代官学的作用。
然而,书院在宋初那种显赫声势的失却并不意味着书院发展历程的中断。恰恰相反,书院在北宋后期呈现出比更快的发展速度。这得益于以士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的支持。民间力量已重回历史舞台,虽无宋初官府势力的强大、热闹,但却实实在在、沉默无声地推动着北宋后期书院的发展。程颢在熙宁元丰间曾建书院讲学,后人以其号称明道书院。程颐则于元丰五年洛阳伊川创建伊皋书院,“以为著书讲道之所,不惟启后学之胜迹,亦当代斯文之美事”(参阅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第92-9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安国楼《嵩阳书院与二程理学》,载《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二、南宋
南宋是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在理学家的引领下,书院与理学完成一体化,同时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统计数据表明,南宋时期的书院总数为442所,是北宋的6倍;即使唐-五代-北宋500余年间所有书院的总和(143所),也只有其总数的1/3。
两宋之际,金兵南掠,加之农民起义,北宋创办的书院多数随战争而消亡。因此,南宋初年一二十年间,书院的建设基本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当国家的命运处于危难之时,大部分由官学培养出来的,素有“四民之首”之称的士人累于功名,见利忘义。价值观的重构势在必行。与此同时,还有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理论挑战。钟相、杨么等农民军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并将其认为天理。这种情形,说明过时的理论必须更新。
为了改变这种士风败坏、人民反抗的现象,理学家们曾作大量尝试,但终因积弊太深,收效甚微:“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见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史资料》)。因此只能另辟蹊径。唐以来的书院正好建于山野之间,能使人远离名利场,安于学业,自然而然就成了理学家们所钟爱的办学之地。
自此,理学家发动了绵延数十年之久的书院建设运动。建炎四年(1130),胡安国从荆门避居湖南,于衡山之麓(今属湘潭)买山结庐,称作碧泉书堂居以讲学授徒。其子胡宏扩建碧泉书堂为碧泉书院,以为会文讲习之所。其时,张栻、彪居正、胡大原等一大批学者云集门下,切磋学术,“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
继湖南理学家开创书院后,各地学者也开始了创建书院、传授学说的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处讲学,带动了各地书院建设。于是,在孝宗时期,尤其是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形成理学发展史上的“乾淳之盛”,为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然而书院运动在宁宗前期,受“庆元党禁”之累,出现了波折。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当权,将理学斥为伪学,严厉禁止。在这种形势下,理学和作为理学家根基的书院倍受冷落。
嘉泰二年(1202),庆元党禁令解除,官府对理学的态度有所转变。嘉定二年(1209),追谥朱熹为文公,为其平反昭雪,即所谓“嘉定更化”。党禁既开,作为理学家大本营的书院亦受到统治者重视。从此,理学和书院一起,一同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民间对于书院的支持更是持续高涨。
在南宋后期,建书院传播理学已成为社会文化主流。
元代:书院推广与官学化
明德识堂·唯邻史卜
元代统治者并非纯粹的莽夫,他们对于儒家文化也十分尊重。元政权创建了24400所各级官学,全国平均每2600人就拥有一所学校。元代对于书院也相当重视,多方扶持倡导,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历史记录。
元书院的一大来源是宋遗民。由于宋长期与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交战,精忠报国的思想为社会所推崇,形成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共识。元初,亡国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忠节之士选择了不与元政权合作的斗争道路。这样,退避到书院讲学就成了众多宋遗民的选择。
宋遗民兴学,直接带来了元初书院的兴盛。建国初期即出现书院发展的高潮,这在整个书院发展史上是一个特例。同时,由于不与元政权合作,宋遗民创办的书院都与现实政治保持了一定距离。而元初三四十年间没有开科取士,科举也不能对书院形成侵蚀,使得书院师生可以专心于讲学、传道。
元代的统治者同样在书院的发展中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元政权前期统治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曾经与其拼死争斗,而现在又拒不合作的群体。面对如此形势,蒙古贵族不得不推崇理学,以“汉化”来重铸文明。因此,他们对研究、传播理学的书院采取了宽容态度。
其实,早在蒙古国时期,他们就关注到了书院,看到了南宋时期书院在统一思想方面的政治功用。窝阔台七年(1235)攻打南宋时,杨惟中等人随军网罗南方学者,收集理学著作,十一二年间,始创建太极书院。另外,为了防止战争对书院的破坏,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下诏:“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读,违者加罪”,对书院等文教设施加以保护。然而,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加之此时的元兵有“屠城”之风,许多书院依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全国统一之后,元统治者重申对书院的保护政策。对于宋遗民兴学,元统治者也予以保护和支持,对他们所创建的书院,一律予以承认,将书院等视为地方官学。经过30余年的经营,到仁宗时期,政府恢复了科举考试,随后“恩赐”六七十岁的做了几十年“遗民”的下第举人任书院山长,入官食禄,进一步扩大了统治基础。
元代,不仅书院的数量快速增长,其分布也有所发展。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南宋失去的领地,再一次为中央政府所有,书院重新建立,其所占份额也超过了北宋,占比全国书院的21.18%。今北京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书院。向北推广是元代书院的一大特点。
元代书院还出现了官学化的趋势。其端倪始见于南宋,主要表现在官学教官时有兼任山长、地方官员兼任书院领导两个方面。到元代,那些在宋代并未形成定制的行为被固定下来。书院的官学化是元代书院发展的一大趋势。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是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而一步步实现的。严格报批手续,以控制书院的创建,是官学化的重要措施之一。从元世祖至元末年开始,创建书院变得越来越困难,申请批复往往需要等待五六年的时间。繁杂的申请审批程序,使得元政府对于书院的控制大大加强,从源头上将书院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书院的官学化既能使书院获取一定的政治力量,也能获取经费、土地,以便更好地教学、传道,其对于书院的发展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日下旧闻》所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指的正是这种情况。
但书院的官学化也有诸多弊端,对书院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吴澄就说:“今日所在,书院鳞比栉密,然教之之师,官实置之,而未尝甚精于选择,任满则去矣;养之之费,官虽总之,而不能尽塞其罅漏,用匮则止矣。是以学于其间者,往往有名无实,其成功之藐也固宜。”(程文海(钜夫)《代白云山人送李耀州归白兆山建长庚书院序》,《雪斋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2册201页)
明代:繁荣与辉煌
明德识堂·唯邻史卜
一、传统书院的发展
明代有书院1962所,前此唐至元元所有书院的总和,也不及其一半。书院在明代出现了繁荣辉煌的局面。
元末,战火纷繁,宋元以来的书院大多毁于战乱之中。明初近百年的书院,基本处于沉寂而无闻的状况。
与明初书院的冷寂相对应的是明代官学的兴盛。《明史·选举志三》载:“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这是明初政策的必然结果。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对书院采取了禁绝措施。与此同时并行的是,大力倡导和发展各级官学教育。建国之初,朱元璋就要求“凭台省大官人用心提调,教各州县在城并乡村,但有三五十家,便请个秀才开学,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读书,不妨他本业,务要成效”。社学的广泛设立,严重制约了明初书院的发展。
另外,明政府极力提倡科举,实行八股取士,并将举业与学校紧密结合。洪武三年(1370)下诏曰:“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宣德以后,又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士人为了考取功名,只能前往学校,书院之学日渐冷清。
尽管如此,书院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恢复。正统以后,地方官绅致力于书院建设的举动,已经影响朝廷,中央政府对于书院的态度逐渐由压制转向支持。
明代书院在成化、弘治年间摆脱困境,步入恢复的轨道。朝庭对书院之设已无禁忌,皇帝赐予院额、令地方官建复书院的事时有发生。其次,宋元时期一些声名远扬的书院得到修复。正是这样一批宋元就享有盛誉的书院的兴复、讲学,带动了各地的书院建设,书院从此即成上升趋势。
成化、弘治年间的复兴,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原因是:学校与科举的结合及其带来的危害。科举与学校的紧密结合,既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也给它的衰落埋下了种子。据《明史·选举制》记载,明中叶以来,科场“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事属暧昧,或挟恩仇报复,盖亦有之”。
这种情况使很多有识之士忧心于怀,不断有人提出整改措施,但不见成效。久而久之,人们对其渐失信心,转而倡导书院教育。于是,久受冷落的书院又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科举与官学的一体化,重建新的理论成为必然。和乾淳之际的南宋理学大师一样,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学术大家从批判官方哲学入手,承担了重振纲常、重系人心的任务。
王、湛之学的崛起是从正德年间开始的,而且和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一样,是和书院一体化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王、湛弟子及其后学建书院,开讲会,倡导各地,又将二者一起推向极致,形成南宋以来中国书院与学术的再度辉煌局面。
明代前期,“书院之建非制也”(杨名斗《武信书院记》,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没有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正嘉以来,当它发展成为王、湛之学的学术基地、宣传阵地以及中下层读书人讽议朝政、要求政治权力的大本营之后,更罹嘉靖、万历、天启三次禁毁之祸,并由此走向衰落。嘉靖初禁,抑制了书院的强劲发展势头;万历再禁,终结了书院的兴盛局面;天启三禁,书院几乎气绝。
崇祯初年,魏忠贤垮台,经御史刘士佐等人疏请,诏令兴复天下书院。但此时的明王朝,在关外清军和关内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之下,已经摇摇欲坠,书院和明王朝一起在兵火中走向灰飞烟灭。
二、书院制度的对外传播
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书院制度的移植始于明代,第一站是邻国朝鲜。朝鲜书院最有力的倡导者,是有“东国朱子”之称的李滉,他上书说:“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所未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朝鲜·李溪《退溪先生文集》卷九,《上沈方伯通源书》)。”他援引《明一统志》所载天下三百余所书院之例,提出了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的建议。“我东书院之作,委于嘉靖年间,逮至万历以后,朝宇之作,岁益浸盛,比邑相望(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四十五,仁祖二十二年八月己未条。转引自丁淳睦《韩国书院教育制度研究》第30页,岭南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民族文化丛书·3》,1989年3版)。”从此,中国书院走上了移植朝鲜的征程,并由朝鲜而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清代:复兴与流变
明德识堂·唯邻史卜
一、传统书院的变迁
清朝是继元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央政权。很多汉族读书人面对异族新政权,在清初做起了明遗民。和数百年前的宋遗民一样,明遗民大多选择了讲学以安栖流血的灵魂。
顺治年间,明福王、韩王等相继建立政权,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亦转战南北,清的统治极不稳固,于是清廷采取了“高压”和“柔化”并用的方针。文化教育方面,推崇理学,大兴科举,创办学校以图笼络人心。于是在顺治“帝王敷治,教化为先”的诏令下,各级官学迅速恢复。但对于书院,由于清初惟恐明末民族主义思想复活,更怕书院聚众反抗,因而百般抑制。
然而,已经实行几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政府强行禁止,颇感困难。因此,到顺治十四年(1657),袁廓宇请求修复著名的衡阳石鼓书院时,朝廷准其所请。由此,各地书院略微有些恢复。康熙二年(1663),随着南明韩王政权的覆灭,社会趋于稳定。清廷极力提倡程朱理学,设馆编修《明史》,纂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几乎网尽天下士人。是时,清政府采取了相对宽松的书院政策,但同时又不解除禁令,意在笼络人心,而又防止书院走向明末清议朝政之路,将书院疏引导入其所设计的发展轨道。
雍正年间,经过一阵犹豫之后,书院政策才开始从抑制转为支持。在雍正看来,各地书院林立,有可能“藏污纳垢”,形成反对派的联盟,危及其统治。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发布正音诏令,福建省政府官员创造性地开始建设112所正音书院,搞得有声有色。雍正对书院的疑虑也因此有所消除。在观望了几年之后,终于在雍正十一年发布了著名的创建省城书院的上谕。省会书院的创建,使十八行省都有了各自的最高学府,这为官办书院教育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乾隆年间,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不再动摇,以创建上下一统,制度完善,定性明确的官办书院教育体系为主要目标。中国书院的等级之塔,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院教育体系。
雍正后期,全面支持书院发展的政策得以确立,民间力量被激活,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书院建设,家族书院、乡村书院不断涌现。于是,官力、民力再度结合,在清代中后期,推动书院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普及性大发展阶段。
到乾隆末年,全国除西藏、蒙古等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外,十八行省已是书院林立。这是继南宋、明朝中叶之后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第三个发展高潮时期。书院的大发展大大推进了文化事业的普及,直接促成了康乾盛世的到来。
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居于康乾盛世之后,又遭外国殖民侵略,更历太平天国起义,内忧外患,国势衰落。但受前期大发展的惯性推动,书院仍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此时的书院尽管气势渐弱,但仍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同治年间,在清代是有名的“中兴”时期。其时,扫荡东南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岳麓书院学生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所指挥的湘军镇压下最终失败,社会恢复稳定,洋务运动渐兴,西学东渐速度加快。书院在社会的巨大期望中也得到超乎寻常的大发展。同时,书院追随时代的步伐,努力适应社会的日益增长并激剧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
甲午海战,中国败于日本,此后人们普遍认为,“时局日急,只有兴学育才为救危之法”,而“整顿书院,尤刻不容缓,此省先变,则较他省先占便利,此府先变,则较他府先占便利”(林增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第49页)。在这种心理指导下,书院改革在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形成了一个高潮。
当时提出的书院改革方案,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即变通章程整顿书院、创建新型实学书院和改书院为学堂。以上三种方案,朝廷一并通行各省督抚学政,参酌办理。于是,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执行,在光绪二十三年掀起了一个改革高潮。
各地书院改革进入高潮之时,戊戌变法运动爆发。光绪皇帝完全采用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的激进办法,限令两个月之内,将全国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戊戌书院改制,从五月二十二日开始,八月初四日以后即不见记载,只有几十天就结束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为了自保,慈禧太后被迫宣布变法,再行“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六月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其中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他们再度重提书院改学堂之议。于是,清政府采用张刘建议,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上谕。
新世纪的书院改制诏令,其前既有名正言顺的借口和台阶,其后又有壬寅学制(1902)、癸卯学制(1904)相配套,因而推行较为顺利,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改制成学堂。除了改学堂之外,还有几十所书院改为图书馆、陈列馆、纪念馆。一些废而不用的书院,也保护起来,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仍在为社会服务。
二、书院的对外传播
顺治初年,东洋日本长崎、滋贺等地开始创建书院。雍正年间,书院又由外国传教士移植到西洋的意大利,由华侨移植到南洋的印度尼西亚等地。而到光绪年间,中国侨民又将书院办到了美国旧金山。
外国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建的英华书院、在新加坡设立新加坡书院、在印尼设立的中国书院等都颇有名气,而最典型的代表则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马戛尔尼访华时就从圣家书院聘用了两个信奉天主教的中国学生,为信奉新教的英国使团提供翻译服务。
三、来华外国人创办的书院
西方传教士在明代后期进入中国,北京首善书院由东林讲学之士的讲会之所,变为汤若望等传教士主导的历局及至天主堂,成为第一个试验西学的标志性场所。但总体而言,西学东渐中,真正有影响的工作由清代后朝的教会书院来承担。
教会书院是在中国的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们,取用“书院”这一中国教学组织形式,加以西方宗教思想理念以及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内容,新创造的一种书院类型。
教会书院成了名副其实的融通中西文化的实体,代表西方文明主要精神的基督教教义与反映东方文明主体精神的儒家思想在这里相聚、相撞、相融,使得它成为近代中国吸收西学的重要园地。虽然教会书院有殖民色彩在其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为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西学东渐作出了重要贡献,科学知识、西方医学和女性教育等,大都经由教会书院传入中国。
当下:书院的复兴
明德识堂·唯邻史卜
时间进入2000年,随着“国学热”的日益升温,催生了各种当代书院或者是新办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书院的复兴跟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是有非常紧密关系的。
“回顾书院发展的历史过程,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如果只有正规学校一种模式,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学习型社会’。书院是中国的一个文化教育传统。对于官学来说,民间的各类书院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补充、借鉴甚至是竞争的作用。我们现在的许多教育问题,如果有了书院的参照,不少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书院既是一个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文化机构,还是一个可以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平台。”
最近十多年以来许多国内高校创办了一些书院,比如复旦大学志德书院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认为,这些书院基本上是为了整合西方学院制度与中国传统书院制度而诞生的。
“因为中国传统书院就有一套师生之间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的形式,注重人格的全面成长。书院的管理方式和西方的住宿学院制度结合起来,把学生的生活事务管理和通识教育结合起来,就成为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的新办书院。这种通识教育和学生住宿管理结合起来的书院,把现代教育和传统书院教育结合起来,使得传统书院的一些精华能够从制度上进入现在的大学体制,来弥补现代大学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过分的专业化。”
2020年7月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明德书院、明理书院成立揭牌仪式,学校党委书记靳诺,校长刘伟,常务副校长王利明,副校长贺耀敏、杜鹏,党委副书记齐鹏飞出席仪式。打破专业边界、整合多学科资源、探索新型教育模式……古老的书院制度,在新的时代,承担起新的使命。
故事,还远远未结束……
写在最后
明德识堂·唯邻史卜
了解程度基本为零的书院、相对不太熟悉的元明清三朝、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庞大叙述……作为一名大一新生,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题目,在短短两三周内成文,笔者也只能尽力为之,也因此本文主要以事实叙述及主流观点陈述为主,但学力有限,争议、疏漏和谬误是在所难免的,还请各位师友斧正。
另外,由于篇幅有限,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未曾提及,比如江西一地的书院数量自宋代开始就领先于其他省,纵使清代有所下滑,但依然位于全国前列。其中的缘由、影响等都值得探讨。另外,许多著名的书院也不曾详细介绍,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明道书院、丽泽书院、西湖书院、东林书院……精彩纷呈的诸多人物往事,实在是力所不及。
希望本文对于各位有所帮助。
主要参考书目:
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
2、 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3、 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上海书店,1991年版
4、 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